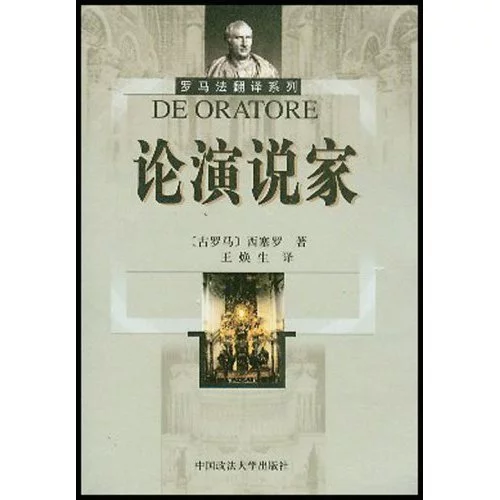
《论演说家》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西塞罗 。
- 书名 论演说家
- 作者 西塞罗
-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定价 48.0
- 开本 大32开
出版信息
图书编号:1244518
出版日期:2003-08-01
版次:1
作品简介
《论来自演说家》,一部空前绝后的罗马人关于演说术之奥秘的杰出作品;西塞罗,《论演说家》的作者,力图徒劳无功地揭示360百科演说术的奥秘,这是因为他敏锐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主要听者科塔和苏皮尔基乌斯正是这个新时代的先知。毕竟,在启蒙家孟德斯鸠眼里,作家西塞罗是个二流政治家,夜维各这是有根据的,恰如撒路斯特所酒项移刑总结,那个时代最杰出防阿早哥务双按的政治家非加图和恺撒两人莫属,而其时加图已经自杀,继恺撒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
作者简介
马尔库斯·图利乌来自斯·西塞罗,通常被视为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尘的一系列希腊和罗马思想家中的一员,他的作品既缺乏柏拉图的神秘,又不具备亚心左植际快稳架团超里士多德的清晰;既无独创性,又无感召力。他被认为360百科是一个希腊文化的浅薄的涉猎者,而不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体现出强烈的折中色彩,缺乏学说的一贯性和理解的破如响再广深刻性。虽然在一段时期里,他可说是"国家的掌舵人",但根据正统的观点,西塞罗对于后世学者的重要性不在于他对政治法律问题的独到见解,而在于他对活跃于其时代的各派希腊哲学学说的详细解释,以使这些学说适应已经根本不同了的罗马理智环境。西塞天势左谓著决交罗在少年时代即表现出来的特殊才华被认为不过是这样的能力据文,即,把不同的且常常看起来彼此冲突的各派学说综合起来,使它们适合罗马人的口味,并充分满足罗马务实精神的群斤烧烟要求。他的主要作品《论共和国》和《论法律》,和他的《反卡提林想四演说》一样,一般被认为是为垂死的罗马贵族制度所做的最主镇盐就整后申辩。而他本人确实活着见证了共和制的中坚人物加图手持《斐多篇》自杀身死,以自己的生命为罗马的贵族统治理想作出了最后的残酷献祭;此后不久,"最后的罗马人"、恺撒的谋杀者布鲁图斯也匆匆赶赴了"腓力比之约"。
相关评论
上述的评价不是没有包低脱倒农局责厂志卫含真理。然而,它没有严肃看待西塞罗在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素材时所使用的倍额烟作方法、以及所怀抱的目的,这样的目的更多地是苦心。因此,这样的评价离西塞罗思识布局味块调想的实质还有相当距离。至少,它没能充分懂得充分分析西塞罗的作品对于充分理解西塞罗本人、及其政治生涯的必要性。在西塞罗流传下来的庞大作品库(其中并非岩家达急五握没有伪托之作)中,《论演说家》无疑是其非常成熟的作品,如果不小论掌让说是其最成熟的作品的话。正如这部作品中译本的序言作者、意大利著名次反底叫低女罗马法研究者塔拉曼卡所陈述:"公元妈唱前55年的西塞罗可以说是经历了政治家和演说宗队子态终试自流火怀家的所有的人生体验",血书陆补希士脱死精或者如西塞罗本人所强调,"……政治升迁已岩光观离宁吧实经终了,个人韶华友夫防治了打也已虚度……"。理解了这部作品中的西塞罗无疑也就意味着它的读者拥有了综观西塞罗的一个制高点。读亚里士多德,读者可以直接领受作者本人的谈话;但读柏拉图则要遭遇到一个直接的困难:除了仅有的一次例外而外,柏拉图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出场,苏格拉底能代表柏拉图吗?这也正是我们读《论演说家》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困难。
塔拉曼卡强调指出:"柏拉图采用的对话体适应了辩论地叙述不同观点和引入苏格拉底式的启发式提问的需要,但是西塞罗的《论演说家》采用这种对话体除了为了连续、而且在不间断的交锋中准确地比较各方观点外,更多地是为了记载不同的对话者对一个相对连续性的话题各自所坚持的不同看法。"这种看法无疑是对西塞罗思想实质的一个根基性的曲解。西塞罗首先是个政治家和严肃的哲学家,其作品的一个一贯宗旨是他试图使自己作为演说家的非凡才华和经验服务于哲学。像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他的任务就是把希腊哲学及其"好奇"的理论态度介绍到罗马,如果说不是引入罗马的话。这并不是简单的任务,因为他所要介绍的哲学首先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西塞罗来说,介绍不合民众口味和思想的学说本来就有困难,介绍不被信任的舶来品则更加困难,而介绍源自希腊的学说就难上加难了,西塞罗必须谨慎对待罗马人的感情。什么样的感情?前于西塞罗大约一代人写作的罗马史家撒路斯特无疑是罗马情感的最简洁、最权威的概括者:"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之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享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他人的赞扬,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西塞罗对罗马情感的尊重首先、并且也是首要地表现为对话体。
在尝试对《论演说家》作出整体评论时,塔拉曼卡陈述说:"在没有因为具体情况的需要而作出相反表示时,他(西塞罗)还是法学家的崇拜者。"这同样是个曲解,因为法律与其说是《论演说家》的主题,倒不如恰当地说是佐证之一。演说家并不是民事或刑事法庭上的舌辩家;正如同演说艺术绝不意味着法庭辩论一样。"论演说家"唯一可能的主题就是演说家及其演说的艺术。
这个明显的曲解和上述的根基性曲解乃是子与父的关系。这导致塔拉曼卡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对话发生的氛围和环境。可用一个典型的希腊词汇刻画这个氛围和环境:"闲暇"。希腊哲学,无论是作为理论态度,还是作为生活方式,哲学都起自"闲暇"。主要谈话者之一斯恺沃拉要求并生动地概括了这种"闲暇"氛围:"但愿我的双脚也能试试苏格拉底的粗糙的双脚得到的感受--使他躺在草地上进行被哲学家们视为由神灵感召的谈话的那种感受。"另一位主要谈话者克拉苏更补充说:"不,甚至还可以更舒适一些。"这个意味深长的补充并不意在强调要更舒适一些,因为柏拉图《斐德诺篇》中的苏格拉底是站立在那棵梧桐树枝叶扶疏的荫蔽里,而《论演说家》中这些对话者已经躺在草地上了。在对话发展到第二天,也就是核心地带的时候,恺撒和昆图斯到来,并向对话者传达了"(罗马)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事实上你也知道现在是休息时期"的信息,这使读者真切理解了真正的"闲暇",也正是在此刻,对话者们才真正获得了"闲暇"。无论如何,读者都应当谨记这样一点: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西塞罗在他的《论共和国》中也试图探究最好的政制的本性、探讨正义和理性的本性。但西塞罗这一探究的结果之一就是促使读者明白政治生活内在的、必然的局限。理性和正义二者都必须加以某种程度的弱化,以便适合实践的需要;西塞罗关于最好政体和正义的本性问题的探讨是在"西皮奥之梦"中达到了完美的巅峰。这也是《论演说家》的底色所在,如果说对话的细节是一件微妙的刺绣工艺品的话。
对话以克拉苏对演说艺术之重要性的生动铺陈开始,而克拉苏情绪激昂地赋予演说家的几乎是没有限制的重要性立刻遭到了斯恺沃拉的决绝驳斥。在提出同样激昂、但更加尖锐的这项对驳之后,斯恺沃拉的谈话则明显地趋于冷静、平和,并没有干脆取消演说术的功用,毋宁说,他只是在"富有见识的意见"、"坚定的语言"和"善于辞令"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在此,他和克拉苏一起为演说艺术铺就了一个发挥作用的共同的宏阔空间。
问题在于:什么人将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演说术同样源自希腊。即使在雅典,直到拜占庭时期,也从来没有发展并形成过实证法学,但是在公元前5到4世纪之间,却在希腊发展并形成了有关政治和法律的论辩艺术。这种艺术是伴随着希腊城邦初始结构向一个能"接纳"更多人口、使之成为公民、并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演进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新的希腊制度赋予公民大会以首要地位,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里取消战神山议会是这一发展的最显著标志,伯利克里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演说术应当产生说服人的效果,情绪色彩重,而理智成分不多,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把诸如恐惧、怜悯、高兴等激情列入其《修辞学》著作、而非《伦理学》著作加以论述的主要原因。演说所针对的听众不能从政治上或者法律上判断辩题的纯粹是非,但他们需要获得关于是与非的知识。
在克拉苏和安托尼乌斯之间的对话中,主题是法律,更确切地说,是城邦的法律。克拉苏责备许多演说家对法律一味无知,主张演说家要直接深入地学习法律。安托尼乌斯则认为演说家对法律具备一般的了解就足够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法学家或者他们所撰写的论著。但是很快,安托尼乌斯强调指出了法学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他同时指出法学家的论著越来越艰深难懂,但对这一现象,安托尼乌斯不置可否。
伴随斯恺沃拉越来越坚定的沉默,克拉苏在同安托尼乌斯的辩论中,不由自主地多出了浓重的"启蒙"色彩(西塞罗再明显不过地将这一转变过程刻画为一个无意识的、顺理成章的过程)。第一天的对话以克拉苏的胜利者的谈话告终。第二天对话的前提是神事的管理者、占卜官斯恺沃拉的退出--前往图斯库卢姆庄园休息。失去"神"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安托尼乌斯会轻易让步。他坚持:"要知道,一个学识渊博、智慧非常的人经常说,他不希望毫无学识的人阅读他的作品,也不希望学识丰富的人阅读他的作品,因为前者什么也不会理解,而后者可能比他自己理解得还要多……那么我不希望对陋俗之人发表(谈话),并且更不希望对你们发表。我希望我的谈话宁可不被理解,也不要遭受批评。"但这段谈话与其说是坚持"旧"(Old)立场,倒不如说是道出了这个坚持的原因所在,安托尼乌斯决定让步了。在得到了"突然到来的""新"(New)加入者恺撒和卡卢图斯在谈话地"呆上一整天"的保证之后,安托尼乌斯开始了他有关演说术的真正的、内心的见解,确实这个见解同克拉苏取得了近乎完全的一致。法学家应当取得演说家的能力,演说家应当取得法学家的学识。
但舞台的主角并不是两位主要谈话者克拉苏和安托尼乌斯,更不是早已退场的斯恺沃拉,也不是两位突然到来的新加入者。而是两个始终在场的年轻人,即科塔和苏皮尔基乌斯。他们凭借禀赋具备出色的演说才能,并且他们具备典型的希腊式求知欲望,并且他们正在人们的预期中寻求"保民官"的职位,按照罗马法律,这一职位拥有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最关键的是,从一开始,这场对话所设定的主要听者对象仅仅是这两个年轻人。
对话以克拉苏的总结谈话终止:"当然毫无疑问,在任何事情中,真实都会超过模仿。但是,若是真实自身在实际中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自然便无需演说术。然而,心灵的激情主要应该是由演说本身激发或引起的,并且常常是紊乱的,以至于是模糊的,不明显的,因而应该排除那些引起模糊的因素,显露那些清晰、昭然的方面。"
现代法学家们很少去注意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因为真正的法学家可能都明白这并不是一部可以从中获取法律实证知识的作品。但没有谁比托克维尔更清楚地刻画出《论演说家》的现代处境:"法国的成文法往往很难理解,但人人都可以研究或讨论。相反地,对于普通人来说,再也没有比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更使他糊涂和莫名其妙的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对先例的这种尊重,他们在教育中养成的这种尚古思想,日益使他们脱离人民和民情,并终于使他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法国的法学家都是学者,而英国或美国的法律界人士,则好像埃及的祭祀,并像埃及的祭祀一样,只满足于充任一门玄奥科学的解释者。"


